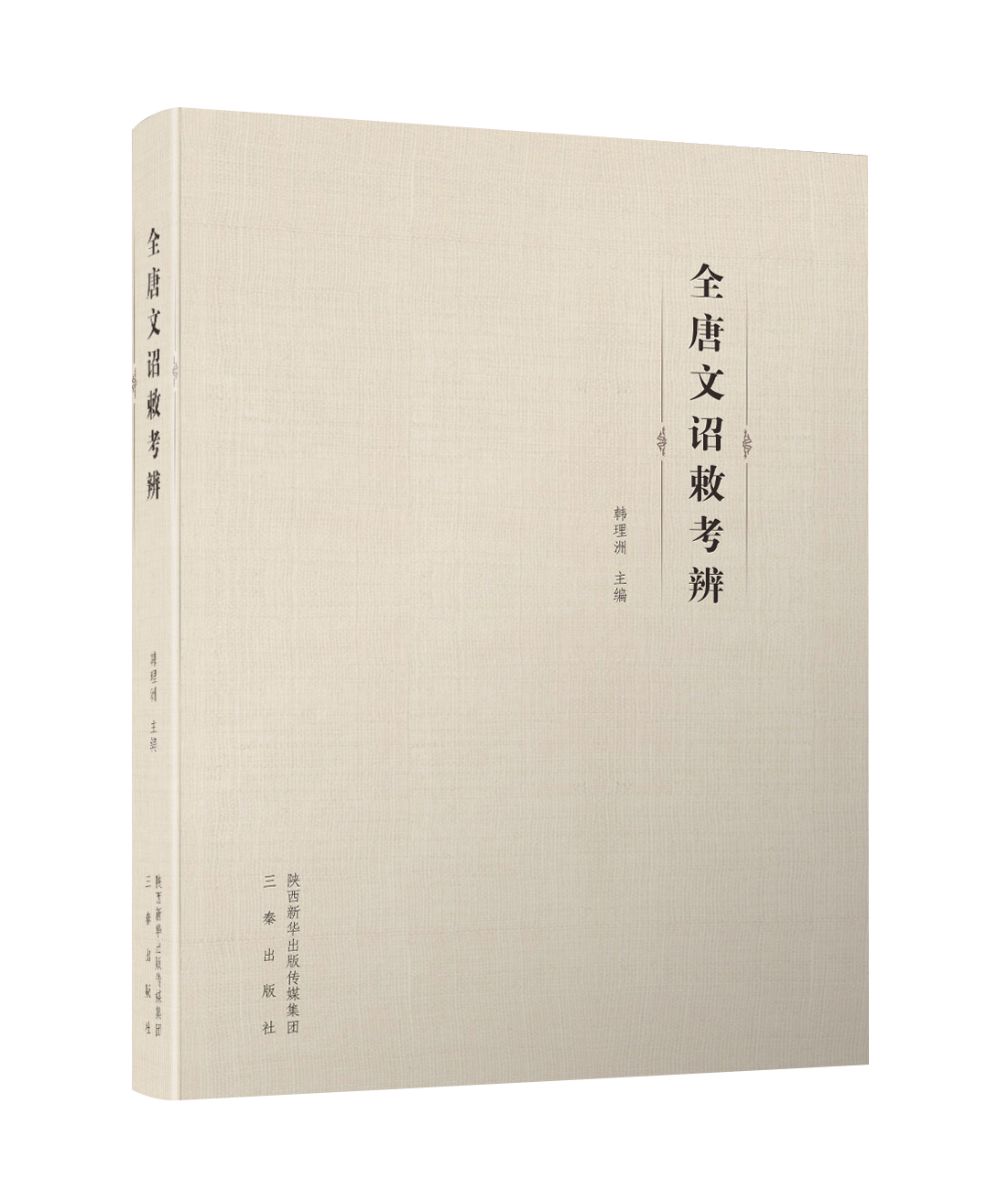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书讯书评 >> 正史纠谬 以资镜鉴——评《全唐文诏敕考辨》
- 评《宋才子传笺证》
- 叶逢春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出...
- 饾版精印与大众画谱之完美结合——...
- 《天下郡国利病书》流传考
- 集前人之大成 启未来之研究
- 一部绣像的汉代史——评《石头上的...
- 一代通儒焦循诗文的首次结集出版
- 真正“包举一生而为之传”的一部力...
- 自从一读《楞严》后,不读人间糟粕...
- 海外寻踪二十年 黑城艺术续新篇
- 一灯能除千年暗
- 孙雄与《道咸同光四朝诗史》
- 从《说文解字》看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 精深华妙 八面受敌——简介李慈铭...
- 中古的科学史、社会史、文化史,抑...
书讯书评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代,其时经济文化之盛、综合国力之强,前所未有。司马光《稽古录》卷一五载:“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然而,唐最为辉煌、最能惠泽后世,也让这个帝国在历史上光彩四溢的是它的文化。正如苏东坡在《书吴道子画后》中所言:“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备矣!”唐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时代文化,且其流光所及,足以为后世企羡。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长足发展的今天,继承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深入研究唐代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唐代文化,《全唐文》是一部不可或缺的文献。这部书是清代嘉庆年间百余名翰林学士用七年时间编纂而成的唐代散文总集。全书共收录唐代作家三千零三十五人,文章两万零二十五篇,囊括了唐代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教育、文学、史学、科技、艺术、宗教、金石、风俗等诸多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全唐文》中的诏敕共有两千余篇,是有唐二十一位皇帝政令的汇集。在“朕即天下”的封建集权时代,诏敕是皇帝发布的施政纲领、政策、命令,是其统治天下的文字记载。《旧唐书》卷四十三《官职二》云:“凡都官掌举诸司之纲纪与官僚之程式,以正邦礼,以宣邦教。凡上之所以迨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这些文字,虽未必出于皇帝之手,或多为骚客文人代笔,却仍是皇帝的意旨,是他处在最高位置,把握全局的决策。众所周知,要从宏观上把握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或者要对某一文化领域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仅限于个别作家、个别作品的研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到当时的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诏敕内容涵盖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吏治、文教、军事、民族、宗教、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大政方针,是当时国家状况的直接反映。所以,研读各个时期的诏敕,是了解唐代社会现实状况的便捷途径,也是了解作品产生背景、触摸各位皇帝思想发展变化脉络的现实依据。如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的“盛世”景象及他在位时为保持政权稳定和富国强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以在诏文中获得相关信息。譬如他任用贤相,在先天二年重用武则天旧臣姚崇就是一例。(《全唐文》卷二十第二百三十六页《授姚元之兵部尚书同三品制》)。他整顿吏治,如《全唐文》卷二十七中所载《整饬吏治诏》,要求每年十月,对官员进行考察“较量”,并将评价结果分为五等,努力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他限制宗教势力,如开元二年二月的《禁创造寺观诏》就是对寺观建筑规模进行限制,命令“自今以后,更不得创造”。在《全唐文》卷三十五第三百八十二页中有《示节俭敕》,也可以看到唐玄宗在提倡节俭方面的努力。唐玄宗还相当重视对宗室人员及其弟子进行管理约束,《全唐文》卷二十六的《诫励宗室诏》中说“皇室子弟未能称职”,要求其“谨身奉法”敦促他们“宜各勉励”。当然,当其年老不再亲历政事,诏文中就显示了其政令失当的一面。这些诏敕都是针对当时特定历史现实而颁发的,也反映了特定的社会现实。
《全唐文》卷帙浩繁,内容宏富,又成于众手,其体例欠完善,错讹脱夺在所难免。如录文不注明出处,作者张冠李戴,正文残缺讹误,重出误收,甚至误收其他朝代的文章。这些讹误,若不加辨析厘正,必会导致谬种流传。后世学者若盲目征引,更会贻误后人。清代考据家劳格深谙唐事,撰有《读全唐文札记》《札记续补》共一百三十条,近代唐史名家岑仲勉先生继撰《读全唐文札记》三百一十条。另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学者池田温编有《唐代诏敕目录》。这些著述,都为深入研究《全唐文》做出了卓越贡献。但错漏之处,还所在多有,需要再加以考辨厘正。为此,西北大学国际唐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韩理洲先生和他的团队,以清编《全唐文》为底本,参照相关文献典籍,对其诏敕部分逐篇编年、考辨、究其错讹,补其缺漏,撰成《全唐文诏敕考辨》一书,旨在对唐代的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有所助益。
本书对《全唐文》中诏敕的考辨做了以下工作:
一、 考证了可编年的诏敕作时
《全唐文》中所收文章均未编年,这给研究者的检索和使用带来诸多不便。本书在广泛吸收先贤和今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大量披检有关文献,考得了绝大多数作品的作年。这些系年,力求证据确凿翔实,力戒主观臆断。凡有异说者,则择其要者客观介绍,凡有取舍,则说明依据。如《全唐文》卷一第二二页唐高祖《置社仓诏》,据《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第二一二二页、《册府元龟》卷五〇二、《唐会要》卷八八第一六一一页记载,该文作于武德元年九月甲子(二十二日),但是,《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第五七九页录本文,题为《置常平监官诏》,篇末署作时则为“武德九年九月”。著者对此未妄作取舍,又检《旧唐书 · 食货志》、《唐会要》卷八八得知,唐高祖曾于武德五年十二月下令废常平仓监官,因此,九年已无此官,《唐大诏令》载《置常平监官诏》作于九年,显然是“元年”的形似之讹。
二、 吸收补充学界研究成果,查明参校本,为读者提供校勘依据
掌握版本源流是整理古籍、用好古籍的首要条件。《全唐文》是以清代嘉庆年间内府旧藏的《唐文》为底本,又广泛搜集唐宋以来的有关文献编纂而成,而今《唐文》已佚、清代学者又未注明诸篇文章的出处,这给后世学者的研读和使用造成了诸多不便。唐代诏敕共两千余篇,本书作者团队大量翻检文献,为其中的绝大多数提供了校勘依据,并且补充了一些研究资料的不足。如日本东洋文库于一九八七年刊行的《诏敕目录》,以辑录诏敕之全、征引文献之众、编排之简明向为学界推重,也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重要线索。但由于唐代诏敕数量众多,检索文献种类多,头绪繁杂,其中一些诏敕的出处《诏敕目录》没有翻检到,本书对此作了不少补充。如《全唐文》卷七一第七五四页唐文宗的《敕礼部侍郎高锴试宗正寺解送人诏》一文,《目录》中只列出《全唐文》卷七一。著者检阅大量资料之后,发现此文又见载于《云溪友议》卷上、《太平广记》卷一八一、《唐诗纪事》卷五二。又如《全唐文》卷七四第七八〇页所录文宗皇帝的《答刘禹锡同州刺史谢表批》一文,《目录》中注明出处只有《全唐文》卷七四。本文指出其参校出处还有《刘宾客文集》卷一六。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诏敕目录》中颇不少,如果仅以其书所列的“昭宗中”的诏敕为例,《全唐文》共录昭宗诏敕六十一条,就有十条可以在《诏敕目录》中所列的参校本之外找到其他参校本。
三、 纠正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全唐文》的张冠李戴现象所在多有,其中诏敕中的误收有两种情况。一是把撰者之文归于帝王名下,二是唐代帝王之间的录文误甲为乙。本书对此做了考辨,仅玄宗文就有如下讹误。
把有撰者之文归于帝王名下的有:
1.《 全唐文》卷二十第二百三十五页录唐玄宗文《受禅制》,《文苑英华》中亦著录此文,但指出文章作者为苏颋。
2.《 全唐文》卷二十第二百三十六页所录唐玄宗文《封张制》,《唐大诏令集》卷六十三第三百四十八页亦录此文,指出作者为苏颋。
3.《 全唐文》卷二十第二百三十九页录唐玄宗文《加刘幽求实封制》,《唐大诏令集》中卷六十三第三百四十九页亦录此文,并指出作者为苏颋。
4.《 全唐文》卷二十中第二百三十五页录唐玄宗文《命张说等与两省侍臣讲读制》,《唐大诏令集》巻一百五中亦载此文,然指出作者为苏颋。
5.《 全唐文》卷二十七第三百零七页录《求言诏》一文,在《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五中亦有录文,作者为苏颋,以上五篇,按照《全唐文》编排体例此文应划归苏颋名下。
唐代帝王之间的录文误甲为乙者甚多,如:
《全唐文》卷八唐太宗《宣慰剑南将士诏》实为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诏文。卷十六中宗名下的《褒天竺国使臣诏》,实为唐玄宗开元五年五月间的诏文。卷十七《赐突厥书》,实为唐玄宗开元五年七月所作,应归于玄宗名下,而非中宗。卷十七《宴集日本国使臣敕》一文,实为唐玄宗开元五年十月的诏敕。卷十六《劳契丹李失活诏》,实为唐玄宗开元五年十一月诏,被误收为唐中宗名下。卷十六《赠党项拓拔思泰特进制》一文,并非唐中宗所作,而是唐玄宗开元九年的制诏等等,恕不枚举。
四、 考查了诏敕中的残篇阙文
《全唐文》所录皇帝诏敕讹夺衍倒时有所见,有好多甚至是残篇阙文。如,该书卷五第六五页唐太宗《水潦大赦诏》、卷一三第一五八页《营造孔子庙堂及学馆诏》,卷六十九第七三三页唐文宗《恤刑制》,卷七〇第七四四页的《更定荐代例诏》、卷七一第七四九页的《追录故中书令褚遂良等裔孙诏》,卷七六第八〇三页武宗皇帝《厘革请留中不出状诏》,卷八一第八四七页宣宗的《停税茶敕》等。诸如此类本书都根据有关文献做了指正。
五、 厘正了重出互见的诏敕
《全唐文》收录的同一篇诏敕,在全书中重复出现的情况时有所见。如该书收录的唐太宗《答房玄龄请解仆射诏》既载于卷六,又见载于卷九。该书卷五十二收录德宗《宣慰河南河北诏》,卷五十四易题为《水灾赈恤敕》,作者将两篇诏文相核对,前者实为后者之节录。此类问题,本书均予考辨厘正。本书的撰写工作从2006 年已经开始,十年磨一剑,实为一部学术精品。此书的出版,必将对于《全唐文》中诏敕的研究起到其独有的作用。
(《全唐文诏敕考辨》,三秦出版社2017 年3 月出版,定价:38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