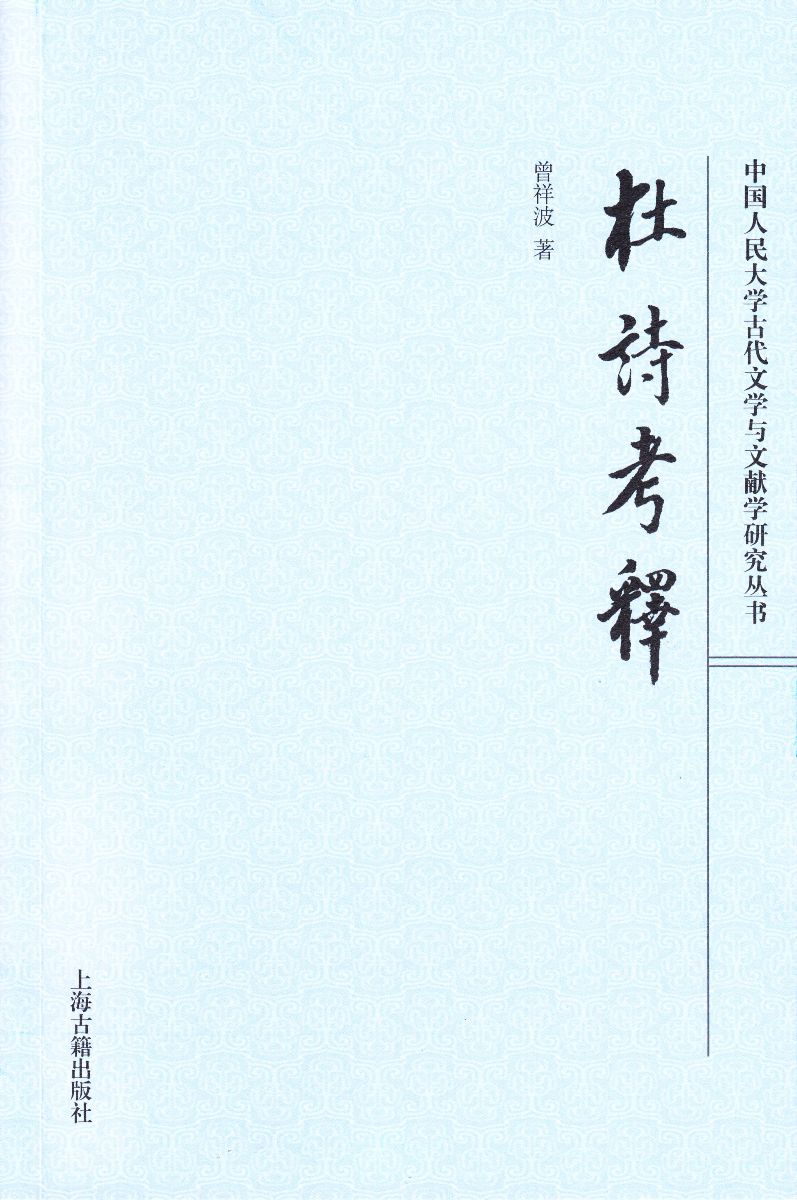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书讯书评 >> 研究理路 阐释诗义——《杜诗考释》出版
- 评《宋才子传笺证》
- 叶逢春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出...
- 饾版精印与大众画谱之完美结合——...
- 《天下郡国利病书》流传考
- 古籍整理可包括辨明其非——读《嬾...
- 一部家族史的代表作——《弘农杨氏...
- 深沉更商量 邃密出新知—读郑利华...
- 《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
- 记《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的出...
- 写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
- 博贯衡综 嘉惠士林——评《缪荃孙...
- 《明史选举志考论》评介
- 先秦卜法的新探索
- 荟萃墓铭 补遗唐文——《昭陵墓志...
- 海防史研究的典范之作——评《重门...
书讯书评







一
杜诗之义大矣哉。宋人有与“六经”并论者,陈善《扪虱新话》称“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鲁訔《杜工部年谱序》则曰“若其意律,乃诗之‘六经’”;蔡絛《西清诗话》以为“少陵远继周《诗》法度”,进而“以经旨笺其诗”。 至于以“诗史”拟之者,更无论矣。虽然,“诗史”之论播在人口,熟在人耳,其蕴义有未尽者。如李格非云:“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若仅以“诚实”视之,则如磨勘簿录、流水日札,仅具撰者个体意义,于他人无涉也。又如李复云:“杜诗谓之诗史,以班班可见当时。至于诗之序事,亦若史传矣。”若仅以“史传”视之,则遣一史官执笔足矣,何以诗为?以余所见,宋人林駉《古今源流至论》“杜诗”条所论,可称圆融妥贴:
白乐天《海图屏风》之作,前辈窥见其心之不忍用兵。刘禹锡《三阁诗》四章,识者谓可以配《黍离》。后之读工部诗者,安可不求诗之意哉?吾观公之气节高迈,秋霜争严,风标屹立,砥柱中流。嗜杀人如严武,则瞪睨而儿戏之。房琯毁师,公乃排众而申救之。而议者不挈置于仁人之列。至于沈宋谗谀、温李淫艳者为伍,前辈深以是为恨,惜哉!夫公之诗盖爱君之盛心也,《北征》之篇,盖仓皇问家室而作也,使或者处之,对童稚,语妻孥,他不暇顾,而终篇谆复,惟及国事,山谷喜之,谓退之《南山》不必作。《登慈恩塔寺》,此正陪诸公游遨而作也,固宜笑谈风月,傲视八极,以乐其心,而措意立辞,意在言外,荆公谓其讥天宝时事,则其爱国之意果何如。‘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夏郑公知其为肃宗,而非为月也。‘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或谓史思明尚在,而非为星也。《石壕吏》之作,韩魏公知其论戍役之苦。‘茅壁’之咏,苏公知其疾藩镇之强。噫!非杜工部之知道,不能发爱君爱国之辞;非苏、王诸公之知诗,不能明爱君爱国之心。是诗也,乌可与骚人墨客同日语哉!不特此也,《百舌》一咏,恶谗佞也。《恶木》一章,伤小人也。腐草之萤,讥阉寺也。寒城之菊,悯士操也。《悲青坂》,伤战败之无功也。《叹秋雨》,刺暴虐之伤恩也。《兵车行》,盖念驱中国之众开边境之地也。《洗兵马》之作,盖言复西京之地、扫安史之乱也。又不特此也,以是心而处已,又以其处已者而待人。其送严郑公也,则曰‘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其寄裴道州、苏侍御也,则曰‘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其寄董嘉荣也,则曰‘云台画形象,皆为扫妖氛’。呜呼,又何待人之厚耶!先辈谓公诗足以历知一代治乱,以为一代之史,则非词人之诗,乃诗中之史也!吕公编《杜工部年谱》,始于先天,终于大历,且与唐纪传相为表里。故凡唐史所未载者,或见于公之诗;而观公之诗,足以历考一世之治乱。又《唐史》云:‘善谋时事,至千言不衰,世号诗史。’先儒作公诗序,又谓诗与唐录犹概见事迹,复许之以为‘诗之六经’。则非特诗中之史,又诗中之经也!
窃以为,杜诗之号“诗史”,有二义在焉:小而言之,为杜子美一生之出处行事、精神心迹之完整写实;大而言之,为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由盛及衰命运之完整写照。要言之,诗史乃个人生活史、精神史与国家、民族史之完美结合。此一标准,就个体诗人的创作而言,吾国诗人惟杜甫臻于极至,其称“诗史”,名至实归。进而言之,杜诗以“诗史”本色为底蕴,兼熔叙事、抒情、技巧于一炉,法度森严而能契合无间,足为唐以降诗歌之典范,视为“诗经”,亦非河汉之言也。
二
笔者对杜甫与杜诗的研究,源于翻译洪业(煨莲)先生《TU HU: China’s Greatest Poe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译本《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于2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著名史学家,洪业先生原来就以杜诗版本研究见长,其《杜诗引得序》迄今仍被视为杜诗版本史的经典撰述;他在《杜甫》一书中集版本研究之大成,进一步以史学家的视角与素养出发,对杜甫行实及杜诗编年、阐释提出了大量新解,这些见解即使置于当今杜甫研究领域也仍具有前沿性。在翻译此书同时及之后,笔者对洪业《杜甫》一书所引近四百首杜诗加以细读,对每一首诗的全部宋人注文、系年编次及代表性明、清人注文、系年编次进行了汇集与比对,进而产生了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对杜诗的原创性理解,基本上都被宋人“千家注杜”囊括殆尽。后世注家往往只是在宋注的基础上加以推进、辨驳或反转,很难再在全局性的高度提出大量的原创性新见—可能唯一的例外是洪业《杜甫》。洪业先生以史学家的身份介入杜诗研究领域,其独特的职业敏感与素养使得他讨论杜诗时必要追溯一切见解与资料的第一源头,而其20世纪20年代所编纂的《杜诗引得》又对杜诗今存几乎全部宋注本与重要元明清注本的版本、编次及注文进行了系统梳理,这就使他往往能够越过明清注家如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杨伦等人已经累积成型的定见,直指宋人注乃至杜诗本文,从而处在与宋代注家平等的位置上考量问题,提出与宋人同等分量的新见。故此书195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后,立即被西方汉学界视为最重要的杜诗研究论著之一,迄今犹然—受洪业思路的启发,窃以为对杜诗及杜甫诸问题的研究,现在不应还停留在讨论所谓“集大成”的钱、朱、仇、杨、浦等清人注的阶段,而要首先回到宋人“千家注杜”这一原始起点,以学术史的眼光将杜诗诸问题的萌生、推进、讹变,以及目前为止已经形成的共识或者谬误,加以正本清源似的梳理清查,从而能够剖析杜诗这一中国文学的经典“箭垛”上“层累造成”的定见,以还原杜诗本文的“纯度”,进而恢复我们对杜诗文本阐释的敏感性。
第二,对杜诗宋注的清理,需要将传统文献的版本目录之学与现代的文本细读方法结合起来。因为宋人“千家注杜”的线索本就极为繁复,文献资料又存佚相参;并且随着文献的传承流变,杜诗宋本还往下一直影响到清人杜集注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还大量存在着有意、无心的抄袭、作伪等问题。因此,在讨论杜诗文献时,传统的版本目录之学已经被动地包含了以讹传讹的大量材料,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的记载来彻底解决问题,这就必须向现代的文本细读方法寻求援助。具体来说,在讨论一首杜诗时,首先要将一切能够找到的关于此诗的宋人阐释集中起来—这不但包括各种宋人注、宋人笔记中对该诗的讨论,还包括一切宋人杜集注本(必要时甚至还要利用明、清人杜集注本)对此诗的编次系年等资料一一加以分析;其次,以此方法对更大数量的、以卷帙为单位的(卷帙往往意味着杜甫生活的某一特定阶段)、涵盖各时期的杜诗加以分析;再次,经过对相当数量杜诗的分析后,得到某些具有规律性的认识;最后,将这些规律性与传统说法、定论进行对比,以确定、推进或者撼动、反驳已经成型的定见,得到新的认识。
总结而言,即三个原则:研究理路上以洪业为师法;诗义阐释上以宋注为源头;版本源流上以编次(系年)为核心。
三
本书以上述三个原则展开研究,内容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为“杜集传谱考论”。阐述杜诗宋本、早期宋注、唐宋时期杜甫《传》、《谱》的文献沿革流变、撰述特点等问题。
上编的主要问题与观点包括:
(一) 《 论杜诗系年的版本依据与标准—以王洙祖本为中心》,提出探究杜诗系年,首先应以遵从校勘学重祖本源流的原则为前提,重视杜集祖本王洙本在系年上的源头性。其次,季节、地理等因素可作为系年的重要标准。这两点在覆核杜诗旧系年编次与探究杜诗新系年编次时,皆可作为基本依据及标准加以应用。
(二) 《 论吴若本与〈钱注杜诗〉之关系—兼论〈钱注杜诗〉的成书渊源》,指出吴若本作为王洙本之后的重要南宋初杜集本,其编次应与王洙本旧次相同。而钱谦益《钱注杜诗》号称承袭吴若本而来,其实暗地里已依据宋人鲁訔编次与黄鹤系年,对吴若本原编次有极大改动,此为文献整理之大忌。《钱注杜诗》向称清人杜集注本的源头性“善本”,考察其成书渊源,对衡量《钱注杜诗》版本的真正价值,对了解清人杜集注本对宋人杜集注本的承袭线索,皆有重要意义。
(三) 《 早期杜集宋注师尹〈杜工部诗注〉的特点与价值—兼论杜诗“自寓”说的源头及其影响》,认为师尹撰《杜工部诗注》与其个人经历有关,成为宋人杜注个性鲜明的一家,其特点是善于体会杜诗深意,好将杜诗与杜甫行实、时事政局相联系阐释,其失则流于穿凿附会。师尹注的特点对宋人及后世杜诗注家有相当影响,如历来争论纷纭的《佳人》“自寓”说即是。师尹揭橥的“自寓”说对探究杜诗某些篇章本意不无启发。
(四) 《 现存最早杜诗编年注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平议》,指出宋人赵彦材《杜诗赵次公先后解》有两大特点:其一为对杜诗系年编次(即以王洙本为主,包括师尹、蔡兴宗等编次的“旧次”)的认定与调整;其二为在对更早杜集异文及旧注辨正的基础上对杜诗义旨的独到理解。其中透露出来赵次公“以史证诗”的外证法与“以杜证杜”(行实)、“以杜解杜”(诗义)的内证法,在早期杜注中堪称典型。尤其是赵次公以“诗家之心”解诗,超越了通常注重事典出处的“学术性”注释范畴,具备了“同行评议”的意味,成为杜诗宋注中独一无二的亮点。尽管赵次公注还存在某些缺陷,但作为现存最早杜诗编年注本,其特点与价值在杜注历史中具有“导夫先路”的开创性。
(五) 《 蔡梦弼〈草堂诗笺〉整理刍议—兼议现存最早两种宋人杜诗编年集注本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与旧题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之优劣》,指出蔡梦弼《草堂诗笺》与托名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作为现存最早的两种宋人杜诗编年集注本,一般认为《杜陵诗史》成书在先,然今存《杜陵诗史》唯一刊本刘世珩玉海堂藏宋刻本有增补递修之迹,其刊刻时间在宋刻五十卷本《草堂诗笺》之后,故《草堂诗笺》实可视为现存最早之宋人编年集注杜集。由于《草堂诗笺》存在蔡梦弼不标明注家主名以及流行于世的黎庶昌刻“古逸丛书”本编次混乱两大问题,故有必要以宋刻五十卷本系统及其他宋人集注本对其加以编次及注文两方面的校勘整理,以期得到一种最早之宋人编年集注杜诗善本。
(六) 《 论宋代以降杜集编次谱系—以高崇兰编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编次的承启为中心》,指出高崇兰编,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首次将杜诗黄鹤系年呈现为文本编次形态,从而成为第一次融合了宋人两大杜集编次系统(鲁訔编次与黄鹤系年)的杜集本,此点尚未被研究者注意所及。因此,高崇兰本可视为宋人杜集编次之殿军,同时也成为元、明、清三代杜集编次的重要源头,此乃高崇兰本于元、明两代最为流行的重要原因,其影响及于近代以来东、西方学术中的杜诗研究。只有充分认识到高崇兰编次本在杜集编次流变中的枢纽地位,才能真正厘清宋代以降的杜集编次谱系。
(七) 《 现存唐宋杜甫传谱考论》,所考杜甫传谱仅限于杜甫传谱的唐宋“源头”时期。自唐樊晃涉笔叙录,元稹撰为墓志铭,两《唐书》录入文苑,宋吕大防首作年谱,至宋人蔡兴宗、赵子栎、鲁訔、黄鹤等人或增或辨为止。在细读传、谱文本的基础上,对各传谱对杜甫行实及杜诗系年的原创性贡献及先后承袭关系作了详细辨析。
(八)《 现存五种宋人“杜甫年谱”平议—以鲁訔〈杜工部诗年谱〉对赵子栎〈杜工部草堂诗年谱〉、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的承袭为线索》,是对《现存唐宋杜甫传谱考论》文本细读的一个小结,指出现存五种宋人杜甫年谱之间相互关系的其他方面及各自的价值(尤其是赵子栎谱在杜诗编年史中的价值与贡献),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认识。具体而言有四点:第一,赵子栎《年谱》撰成时间当在鲁訔《年谱》之前,与蔡兴宗《年谱》相互独立完成;第二,鲁訔《年谱》完全吸收了赵子栎《年谱》的原创观点;第三,鲁訔《年谱》对蔡兴宗《年谱》的吸收,一方面不但如林继中先生所说表现为基本结构框架的承袭,另一方面还在于鲁谱全部采纳了蔡谱的原创性观点;第四,就承袭前说而经辨析后自出新解这一层面来看,黄鹤《年谱辨疑》的原创性贡献远远超过鲁訔《年谱》,却未曾得到相应重视。总的来说,鲁訔《年谱》在五种宋人“杜甫年谱”中原创性最低,其声名显赫,一方面在于集成汇总(此点针对鲁谱全盘吸收赵子栎谱、蔡兴宗谱的原创观点而言),另一方面乃是因为两种现存最早、影响极大的杜诗宋人编年集注本(蔡梦弼《草堂诗笺》、托名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皆以鲁訔《杜工部诗年谱》为基本编年框架(此点针对黄鹤《年谱辨疑》而言,因采用黄谱的黄氏《补注杜诗》乃分体本而非编年本,不利于读者阅读与使用)。揭橥鲁訔《年谱》对赵子栎《年谱》的承袭,不但可以弥补宋人撰“杜甫年谱”由蔡兴宗谱到鲁訔谱之间缺失的一环,还能进一步厘清现存五种宋人撰“杜甫年谱”的价值及相互关系,并重新审视唐宋时期“杜甫传谱”的基本格局。
(九) 《 杜甫二子考》,在洪业新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关于“杜甫二子”的传统说法“大儿宗文小字熊儿,小儿宗武小字骥子”是错误的。梳理考辨杜诗,可知杜宗文字骥子,杜宗武字熊儿,宗武出生于至德二载秋八月杜甫奔赴肃宗行在之际,此时杜甫不在家中,未能亲见其出生。由此,杜甫离家奔赴肃宗行在的某些具体情势以及若干杜诗中传统注释的龃龉之处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十) 《 李杜关系新说—以杜诗对“偶然性细节”的刻画为视角》,通过天宝四载李杜同一题材(“寻范十隐居”)的诗篇比较,指出“重与细论文”体现的是杜甫对于李白叙事艺术中对偶然性细节刻画的推崇,是讨教而非指斥。众所周知,乾元二年(759)三月,杜甫西返华州,途中目睹人民受战争苦难,连续写下名篇《三吏》、《三别》,标志着杜甫思想境界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为人所知的是,与杜甫思想认识上的成熟相互应和,乾元元年年底杜甫由华州东进洛阳途中,诗歌叙事中的细节刻画技巧突然有了一次集中的爆发,其中体现出善于发现生活之巧的眼力与跌宕腾挪的表达技巧,表征了杜甫诗歌叙事的成熟,这可能与他在天宝四载(745)山东时期对李白叙事艺术技巧的讨教与学习有关。
下编为“杜诗选释”。宋人姚宽《西溪从语》卷上说:“或谓诗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类,故名诗史。盖唐人尝目杜甫为诗史。”杜诗非但为一国之诗史,亦为一人之诗史,故下编在洪业《杜甫》一书所选近四百首诗篇的基础上,进一步选取具有与杜甫个人行实、唐代史事最相关,宋人讨论分歧较多的代表性杜诗一百十七首,以编次(系年)为核心,以宋注为源头,汇集诸家注释及于“年月地里本末”者,分“系年”、“题解”与“笺释”三部分加以考释。
杜诗研究著述分为上、下编—其中下编为诗选注,是上编的文献基础与例证来源—这是现代杜诗研究著述的一种常见体例。另本书引文中出现的异体字予以保留。书稿刊行,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
笔者读杜有年,然子美诗渊深广大,千家注杜,各取一瓢,滋味万般。拙编自引一端,崇其所善,或如煮山中白石,方其操觚,言之津津,及至享呈,淡乎寡味,又似空谷行迹,难获蹑者,况兼才识卷娄,必有疏谬。读者审明,当有以教我也。业师袁行霈先生允为本书题签,是学生之幸,并以志之。
(《杜诗考释》(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11月出版,定价:11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