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业界动态







本文原刊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0年第10期
今年是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收官之年,也是2021—203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谋划之年,对于古籍出版同行来说,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关乎到出版社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由此,笔者想结合近期参加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古籍办”)关于制订2021—203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调研工作,以及自己主持凤凰出版社制订和实施前一个古籍出版十年规划(2011—2020)实践,就其体会与认识,从出版的角度,谈点看法,供同行指教。
2009年8月,古籍办下发《关于申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的通知》,开始编制新一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项目申报采用出版单位、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有关古籍整理专家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办法,经古籍办组织专家反复论证,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于2012年7月,正式下发《关于印发实施〈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通知》,共计491个项目入选。其后,经过2013、2014、2015、2017、2018年五次调整、增补,共计677项。这其中,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工委”)40家成员单位承担了510项,占75%以上,其中超过20项的有六家出版社,都是专业古籍社,分别是中华书局(115项)、上海古籍出版社(86项)、凤凰出版社(50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5项)、黄山书社(24项)、齐鲁书社(23项),可以说,古工委是这项规划实施的“主力军”。可以预期,下一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年(2021—2030)规划”,仍将是这些出版单位,特别是其中的专业古籍出版社,成为规划项目出版的基本队伍与主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古籍出版事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出版过一批能够传之久远的古籍整理图书,可以称之为“新版经典古籍”,这些新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都与不同时期国家层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有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共制订和颁布了七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分别是:(1)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制订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2)1981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制订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共计7类3119项;(3)1992年制订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年—1995年—2000年)》,共计8类1004项;(4)1996年又制订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1996年—2000年)》,共计9类392项(加上丛书子项目在2000余项);(5)1999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调整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2001年制订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年)重点规划》,共计8 类207项(加上丛书子项目在800余项);(6)2006年,制订了《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共计8类196项(不含未统计的丛书子项目);(7)2012年,制订了《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同时,1983年,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成立,也制订和设施了若干古籍整理规划,虽说高校和出版分属不同系统,但在项目上大多是衔接的,主要是整理与出版的“上下游”关系。上述诸规划,对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起了极大作用,催生了一大批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以2013年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首批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为例,共计91部,其中有55部列入了上述6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不包括第一个“草案”),如再加上五年一次的国家重点图书选题规划、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规划(可参见杨忠主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高校古籍整理十年》第334页“重点规划项目”一节),入选图书基本都是国家层面上各级规划项目。因此,对于古籍出版单位来说,制订和实施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既是初衷和使命,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之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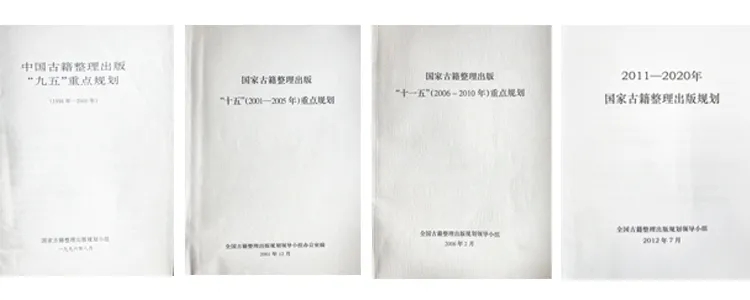
一、实践中的几点体会。
笔者所在的凤凰出版社,原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更名。刚更名时,出版社只有18人,至今也就50余位员工,是一个生产和经营规模都很小的出版社,但我们选择了更名不变初心,坚持古籍专业出版,首先抓的就是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特别是利用申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契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选题特色与出版优势,并获得同行认可。列举十年间(2011—2020年)几项数据为例:国家“十二五”“十三五”重点选题规划,分别为20项、19项;《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50项、国家古籍年度专项资助70项;国家出版基金23项、中国出版政府奖(古籍类)4项。由此,笔者在实践中体会到,对于中小古籍出版单位,中长期专业选题规划所具有的引领作用尤其重要。归纳而言,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出版社明确定位。所有出版企业经营者都强调企业发展定位问题,在出版单位由事业身份改成企业性质后,貌似站在同一起跑线,但由于出版社成立时间有先后、规模有大小、分工有差异、隶属有不同、资源有多寡等历史客观因素,实际上不可能有统一的出版企业定位,都是依据各自实际确定。笔者认为,对于中小出版企业,特别是古籍出版单位,由于受制于多种因素,特别是各地集团化以后,内容生产多元化路径并不适合大多数古籍出版单位,反而专业出版定位,可以使这样的出版企业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小而美”或许可以成为这类出版企业的追求目标。以古籍出版为例,除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外,地方古籍社大多属于中小型出版企业,经营者都会碰到“做大”与“做专”之间的艰难选择,面临两重压力。笔者曾经历过一件事,2007年,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公布,凤凰社《册府元龟》获古籍类正式奖(共4项),有上级主事者来询“册府元龟”四字意思。笔者由此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凤凰社的选题,要做全集团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做不了,甚至连书名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就有存在的价值与发展空间。”至今笔者仍坚持,与其追求无实之“大”,不如追求有名之“专”。制订和实施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恰恰可以解决古籍出版企业发展定位问题。图书出版是以内容生产为主要特征,选题规划是定位的前提,从选题规划入手,在选题规划中体现企业定位,明确出版社的发展方向与追求目标,对古籍出版社,特别是地方古籍社来说,不失为一种可为的选择。

二是有利于出版社发挥专业出版优势。古籍出版社的人才结构,大多偏向专业型,尤其编辑都受过严格专业学术训练、有各自专业学术背景且学历较高,了解古籍整理图书基本特点与学术规范。制订和实施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可以把他们的专业知识与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有利于发挥其专业优势。理论上所谓“复合型人才”毕竟是少数,学有专攻,志有各向,面对现今各种诱惑,选择古籍出版的从业者,大多专业思想牢固,学术出版是其追求。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恰好与他们理想追求合拍,一方面可以人尽其才,使出版社古籍整理图书编辑质量优势显现出来,将编辑人才优势体现在选题优势、出版成果上;另一方面,编辑通过规划项目实践,将专业学术理论知识转化为专业出版能力,形成古籍出版社特有的人才结构。当我们至今仍对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老一辈“学者型编辑”怀有敬仰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编辑人才,在各方面条件都好于以往不知多少倍的如今,为什么会少之又少?
三是有利于出版社突出工作重点。作为一个曾经主事地方古籍社十多年的过来人,对此深有感触。一个出版单位,工作千头万绪,尤其身为在集团内的中小专业出版社,压力更大,领导有要求,员工有诉求,谁都知道“走自己的路”的道理,但在如今的现实出版环境中,要真正做到淡定和从容又谈何容易。当然,如果撇开这些,中小古籍出版单位,以中长期古籍出版规划为抓手,作为工作重点,或许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凤凰社对此也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同样有上述困扰与彷徨,最终通过制订和实施中长期古籍出版规划,至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通过规划这项重点工作将古籍专业出版定位加以落实。二是通过规划,一批年轻编辑,在古籍出版专业领域有了很快成长。出版定位,需具体项目支撑,并通过不同路径加以实现,凤凰社近十年间(2011—2020年),出版了包括《文选旧注辑存》、《李太白全集校注》、《历代赋汇》(整理本)、《江南通志》(整理本)、《京剧历史文献汇编》等数十种大型古籍整理图书,逐渐形成了凤凰社内容生产重点板块和优势板块,在古籍出版领域获得了学术界和同行认可。至于第二点,一般而言,列入国家古籍整理中长期出版规划的项目,学术性强,难度大,编辑出版要求高。对于年轻编辑来说,高起点有利于成长。因此,我们实行规划项目负责人制,根据各人专业或选题来源,几乎所有年轻编辑都作为一个或多个项目负责人,所有编辑出版环节,均由项目负责人统筹,通过这种形式,年轻编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与成长。目前,凤凰社古籍整理专业重点项目,几乎都由80后编辑策划、组织和实施,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全国同行中也逐渐崭露头角,或入选国家、省级人才培养工程,或晋升高级职称。

四是有利于保障出版经费。不少人对于实施“规划”项目的经费投入有所顾虑,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对于古籍整理这类“小众”图书,在短期内,投入和产出未必成正比,所谓“叫座不叫卖”。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以笔者个人实践中的体会,有这么几点认识:一是如今的出版社,包括中小型规模的专业古籍社,经济状况较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要好很多,就以专业古籍社为例,单从经营上来说,虽然不能和以教育、少儿或综合性的大学出版社相比,但年利润多则在数千万元,少则也有百万元,不存在过去“没钱出书”的窘境。出版社经营者在经营上的压力,并不是有无经费出书的问题,更多的主要来自于作为企业每年不断增长的销售和利润指标考核,客观上造成一些古籍社在专业出版,特别是在实施中长期规划上有所顾虑。二是对于图书这样的“小成本”投入的商品,中国市场足以解决其产出问题,惟有内容质量精品化为前提,小众专业图书的“大市场”,在现实中也有很多。三是国家在相关政策导向上,明确对规划项目扶持。例如,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2009年下发《关于申报2010—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的通知》中,明确列有“今后每年古籍整理出版补贴,主要资助列入2010-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项目”,在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下发的《关于申报2020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的通知》“申报重点”中,也明确“已列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项目”,这些政策和措施,很好地帮助了古籍出版单位在规划项目上的投入问题。笔者所在的凤凰出版社,凡列入规划项目的,几乎都获得国家出版资助。
二、工作中的几个难题。
一是现行出版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古籍整理出版长远规划。目前国有出版企业绩效考核都是年度的,对经营者实行所谓任期制(大多是三年一个任期),经营者的绩效都要在任期内认定,即便有长期激励,也大多是经济指标上,这就给需要较长时间整理与出版的古籍整理选题,特别是需要提前规划、长期实施的项目,在客观上都造成很大难度。
二是由于古籍整理图书的特殊性,整理与出版周期相对比较长,有些古籍整理图书,从整理到出版,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笔者曾对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3年公布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进行了统计,在91部入选图书中,有超过20部的出版时间在10年以上,有9部图书的出版时间跨度在30年以上,最长的近50年。对于这些前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古籍整理项目,对每一位古籍出版企业经营者来说,都是不小的难题。企业经营者在自己任期内,对只有前期投入而不能出版的项目,有所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对制订与实施中长期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
三是在出版企业“做大”与“做专”之间的艰难选择。两者在理论上并不矛盾,实践中也有成功的案例,但以笔者观察,行业中所谓成功者,大多并非来自专业古籍出版企业。目前对于出版企业,“做大”远甚于“做专”受人待见。古籍整理图书小众化特点,使从业者在二者之间面临更难选择,所谓“事非经过不知难”,非古籍出版同行,很难体会这种选择的艰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坚持古籍专业出版是制订和实施好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的重要前提。
四是数量与完成率的问题。对一个古籍出版单位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项目过多,或有些专业学术领域,超出了自己的实现能力,影响企业发展;一是不够重视,项目过少,体现不出专业出版特点,出版内容板块重点他移,看似企业规模做大了,但空有“古籍出版”之名,有违读者期待。如何平衡二者关系、如何选择企业发展路径,做到“两全其美”,确实也是一大难题。
三、思考中的几点认识。
首先,我们认为,自人类有出版活动以来,几千年过去了,简帛纸电、抄写刻印,出版发展多是革命性的,但人们对其需求,基本保留了从中感知历史、获取新知、享受快乐,由此而言,出版的积累与传播、教育与认识、审美与娱乐三大基本功能,并没有也不会因业态发展、转型而丧失,因此,出版本质中的内容特征,要求我们认识、重视和做好出版规划。
其次,出版的内容生产过程,也是一种“选择”活动。什么样的内容将成为出版需要,显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近一百年前,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说过一段话:“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譬如,吾人如用尽头脑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的利益,定非浅鲜;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陆费逵《书业商之修养》,《陆费逵文选》第115页,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出一部有价值的书”,需“用尽头脑和心血”,足见“选择”在出版中之艰难。出版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其中有一条,即对出版物内容慎重精心选择,是其生命力长久保证。由此来看,“出版规划”,就是一种选择。
再次,古籍整理与出版的特殊性,也要求我们从事这项工作,首先要从规划入手。中国古代典籍遗存众多,目前尚未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据《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了17万种左右,这些典籍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态也各有不同,内容更是包罗万象,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并非都是现今社会之需求,选择就成为必然,有所选择,即有所规划。由于古代典籍生成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社会与生活、语言与文字、观念与制度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不同,哪些古代典籍具有当代社会价值与文化观念,哪些又是具有学术文献价值与传承意义,这在古籍整理与出版中必然是会首先碰到的问题。另外,古籍整理专业性强,许多典籍整理难道大,但从出版角度而言,它又属于相对小众的阅读需求,出版与需求之间也存在一个如何规划的环节。上面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出版单位是古籍整理图书出版的绝对主力军,其中专业古籍出版单位更是发挥了专业优势,随着现代出版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些古籍出版社,不但有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更大的空间,更理所应当将自己的工作重点与国家文化战略、出版政策导向相衔接,否则,作为古籍出版单位,我们的工作将失去重点、意义和价值。
第四,要有长远发展的出版观。规划本身就是有一定时间长度的概念,加之出版本身也不是一件急功近利的事情,特别是古籍出版规划更要有长远考虑。匡亚明先生曾经说,要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必须要有“三心”,即信心、决心和恒心,即说明这项事业不能是短期行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对国家来讲,是需要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事业;对每一个有志于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来讲,是终身的事业”(转自李国章《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概述》,见《古籍整理出版十讲》第42—43页,岳麓书社2002年10月版),可见由于古籍整理出版自身特殊性,要求从业者必须要有长远眼光与长期坚持,要有古籍出版“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事业情怀。
明年是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40周年,目前,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在以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对编制2021—203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建议和意见。这些对于古籍出版单位来说,都是莫大的机遇,古籍出版人应该以更多的智慧、更强烈的事业情怀与奉献精神做好这项工作,以不负我们这一代古籍出版人的历史使命。

凤凰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编审。现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主持《江苏文库》编辑出版。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物”、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