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业界动态







8bd0e01abca7690c3ebef1bab907d78f0810520c7b90a30d50086b04bddb87f84ddd6ba1d15a&mpshare=
1&scene=23&srcid=1220zVjv8n8r7ya5Qp9Q8pBs#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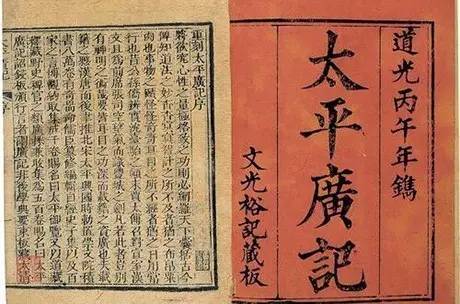
汪绍楹先生对古籍整理做出了很多贡献,可是知道他的人很少。我和他只见过两次面,就是为重印《太平广记》而商谈出版说明的改写问题。《太平广记》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汪先生点校的,1959年出版时书前说明只谈到该刻本有两次印本,对点校工作谈得很简略,而且没有署点校者的姓名。1961年,这部《太平广记》随着一批其他书稿转给中华书局后,准备重印。我们循例请原点校者复核一遍,改正了一些排版上的错误,并修改了出版说明。汪先生跟我讲了讲刻本有三个不同印本的情况和校勘的做法。我们建议他把这些写入由他署名的点校说明。汪绍楹先生为人非常谦和,虚心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对点校说明作了改写。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太平广记》的几种重要版本,得到了不少新的知识。当时为了掌握确切的版本依据,自己也到北京图书馆复核了几卷。我对《太平广记》的版本问题很感兴趣,后来又利用假日去北京图书馆复核了几种版本,作了一点儿笔记——当时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星期日也开放。我曾萌发了重校一遍《太平广记》的想法,但是限于主客观的条件,始终没有可能实现。直到1986年,我把当年的笔记整理成一篇文章,后来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这还是从汪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
汪绍楹先生没有固定职业,当时应出版社之约点校一些古籍,近乎给人打工的做法。我记得当时一般的标点费只有千字三角钱,《太平广记》校勘的工作量比较大,也不知按什么标准付的。中华书局古籍重印时也没有付印数稿酬的制度,可能付了一些修订费。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时没有给点校者署名,也是当时习惯的做法。至于整理的方法,只校改了少数几个显著的错字,一般的异文不出校。当时的风气是,出校异文就说是繁琐校勘,力求简明乃至简单地只以底本为准。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太平广记》的校勘工作不免有因陋就简的做法,因而造成了一些遗憾。然而汪先生的校点工作是很认真的,在异文的取舍上也显示了他的学识水平。
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太平广记》还是以他的校点本作为最可靠实用的版本,许多新版本实际上只是翻印这个点校本而已。那时候古籍整理者一般都不署名,只由出版社写一个出版说明。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请汪绍楹先生点校的《艺文类聚》,则除了出版者的前言以外,还由汪先生写了一篇《校艺文类聚序》。这篇序言充分体现了点校者的功力和水平。汪先生通过校勘,判定底本已有缺佚、窜乱和妄改。点校本“计据他书及冯舒校本(详后)作校记的,约一千六百多条;径据明本改补的,约一千三百多字。两共三千条左右”。整理者见到的有七种刻本,经过比勘,或同宋本,或同胡序本,以胡缵宗序本最为妥善。因此在校勘中,只采用胡序本与宋本比勘。此外,还采用了冯舒校本。冯氏所据钞本,反有胜于宋本的地方,所以采用了大部分。汪先生根据宋本讳字的杂乱,怀疑现存宋本是南宋末或元初间的覆绍兴间刻本,或至少是个补版的次印本。这些地方说明校勘者对于版本有自己的判断,主要是从逐字逐句的校勘中得出的结论。因此,胡道静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类书》中曾一再引用汪先生所写的《校艺文类聚序》,以代说明。
当然,汪先生还指出,“对某个本子好坏的评价,不当仅以刊刻或抄写的年代早晚作衡量的。例如《四部丛刊》影印《鬼谷子》用明《道藏》本,《吕和叔文集》用述古堂抄本,实际上都有脱缺,反不如后来秦恩复刻本的完备”。这些都是来自校勘实践的真知灼见,足见汪先生真是一位博识多闻的版本学家。他在这段话中,附加了一条注文,引录于此,以备读者参考:《鬼谷子》,《道藏》本《内揵》篇脱四百余字,其他脱讹尚多(见《抱经堂文集》十。《丛刊》初次印本,《鬼谷子》用清秦恩复覆《道藏》本。重印时改用明正统《道藏》本。按秦氏刊《鬼谷子》亦两次。先用《道藏》本,后知有脱讹,改据述古堂钞本重刊。《丛刊》用《道藏》本,不用秦氏重刊述古堂钞本,当以藏本在钞本前,认系善本);《吕和叔文集》,述古堂钞本,卷六脱《刘公神道碑铭》,《韦公神道碑铭》二首,卷七脱《郑夫人墓志》等五首,秦刊本具存(《丛刊》舍秦刻本用述古堂钞本,当亦同《鬼谷子》,以钞本在前为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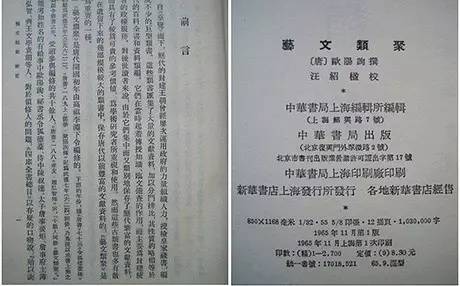
汪绍楹先生校《艺文类聚》,由中华书局出版
从这一条注文,就可以看出汪先生对古籍版本有非常精深的学术素养,决不是临阵磨枪的打工者。也许可以说,他是一个古籍整理的“专业户”。汪绍楹先生整理的古籍很多,除了《太平广记》、《艺文类聚》两部大书以外,还有《搜神记》、《搜神后记》等,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或其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约的稿,转到中华书局后压了好多年。直到1978年,我们才发稿出版,这时汪先生已经去世了。《搜神记》的今本源流不明,真伪莫辨,一向成为疑案。鲁迅说它“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余嘉锡则说:“余谓此书似出后人缀辑,但十之八九,出于干宝原书(此但约略就其可考者言之)。若取唐宋以前诸书所引,一一检寻,尚可得其出处,与他书之出于伪撰者不同。”(《四库提要辨证》)汪先生在校注时广征博引,逐条与各种典籍他校,考源钩沉,寻求旁证,对本书的真伪作了切实的考订。虽然有若干条未见他书引作《搜神记》,但是已经可以说明其“与他书之出于伪撰者不同”,大致与余嘉锡先生的考证相近,只是能确认出于干宝原书的还不到“十之八九”。
《搜神记》出版之后,很受读者欢迎。第一版印了五万二千册,不到一年就卖完了,第二年就再次印行,到1985年第三次重印,已印了近二十万册,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们继续发了汪先生整理的《搜神后记》,也印了不少册。据我所知,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时都是预付稿酬,类似一次性买断的书稿。现在出书后销路很好,学术界的反应也很好,我总想送几本样书和补发一些稿酬给作者的家属,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他家的后人,这事也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听说,汪先生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家庭生活十分优裕,始终没有就业,后来家道中落,所以就当了一个古籍整理专业户。汪先生整理的古籍,至少还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昭昧詹言》。此外,可能还有一些没署名的。我希望有知情的人能多介绍一些情况,以表对这位为古籍整理做出过不少贡献的专家的敬意。(《书品》,2003年第6期,中华书局)

太平广记(1-10册)
作者: [宋]李昉等编
书号:9787101007336
定价:398.00元

新辑搜神记 新辑搜神后记(上下册)
作者: [晋]干宝 撰、[宋]陶潜 撰,李剑国 辑校
书号:9787101051162
定价:9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