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业界动态







http://www.zhbc.com.cn/zhsj/fg/news/info.html?newsid=402885965426c97201542c045ba7007f
就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而言,“十三经”可以说超过任何一部典籍,顾颉刚先生称之为“吾国文化之核心”,“中国二千余年来之文化,莫不以此为中心而加以推扬”[1],所以在整理和传刻方面,历来倍受重视。尤其是清代经学大盛,注疏之作,远迈前贤。自章太炎、梁启超起,即有重订经疏之议。1933年陶湘等创议汇刻“十三经义疏”,1941年顾颉刚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主持印行“十三经新疏”,但限于条件,拟目既定,未遑措手。中华书局自1920年代《四部备要》遴选清人“十三经”注疏首次整理排印之后,于1960年代提出“清经解辑要”出版计划,广纳众议,历经周折,最终形成了“十三经清人注疏”丛书,于1980年代开始陆续整理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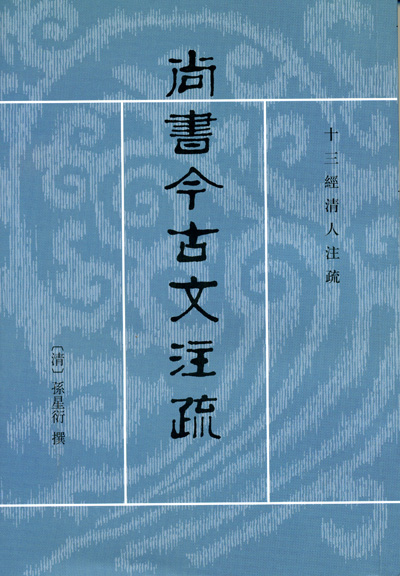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古代典籍的整理和出版一直受到国家主要领导人和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资治通鉴》和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54到1956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由顾颉刚、聂崇岐、王崇武等12人组成标点小组,完成了《资治通鉴》的整理。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2],后来由毛主席直接部署,经吴晗、范文澜、金灿然等筹划安排,于1958年正式启动,次年第一种《史记》出版。
相对于历史典籍,被划属哲学范畴的经部典籍的整理,受关注和重视的程度明显不够,或者说,能否出、如何出,在当时颇成为问题。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华书局改组为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社。当时,中华书局编辑部分为历史一组、历史二组、文学组、哲学组,据陈金生先生回忆,当时哲学组的中心任务是整理出版一套“中国历代哲学名著基本丛书”,但是具体出版物并不列丛书名,包括后来列入“新编诸子集成”的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吴则虞点校《晏子春秋集释》,列入“道教典籍选刊”的王明《太平经合校》,以及列入“理学丛书”的《叶适集》、《何心隐集》等,都在这个系列计划中。另外还与中科院历史所思想史组合作,编辑出版《中国唯物主义哲学选集》和《中国思想史料丛刊》,着手编辑《王夫之全集》等[3]。哲学组的组长由副总编辑傅彬然兼任,这一时期中华书局经部和子部典籍的规划出版,大多与他有关。
1957年,中华书局用《四部备要》旧纸型重印了《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全40册。“十三经”新本的整理工作,随着《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的制订和颁发逐渐展开。1960年3月24日,顾颉刚先生给傅彬然信[4]:
彬然先生:
昨接电话,敬悉一切。
二十年前,客居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其时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设立史地教育委员会,邀我参加,嘱我定出整理“十三经”工作的计画,我就写了《拟印行十三经新疏缘起》及《整理十三经注疏工作计划书》两篇寄出。但后来此事交给国立编译馆办理,我即未与闻。胜利后,编译馆复员回南京,不幸舟覆江中,此项稿件损失甚多。惟焦循《孟子正义》一种交我审查标点,留在我处,幸而获免。现在把旧作二篇、焦书一部送上,敬祈检览。焦书系李炳墋同志所点,他现任合肥安徽师范学院教授,如可出版,请径与接洽。
敬礼!
顾颉刚上1960.3.24.
信后附顾先生1941年所写《拟印行十三经新疏缘起》及《整理十三经注疏工作计划书》的抄件。傅彬然于次日收到此信,有如下批注:“顾所拟与我们设想基本相同”,“请童老(引者案:即童第德,哲学组编辑)提意见。彬然25/3”。这里所谓“与我们设想基本相同”,是指“十三经新疏”,“新疏”即清人经解著作。顾颉刚《为编十三经新疏致专家函》说:“逊清一代,经学昌明,学者奋其精思,不辞劳瘁,往往以一人之力综合前修百世之功,纵有未密,亦已十得七八。爰拟先取此类巨著,汇刊一编,名之曰‘十三经新疏’”。所列书目,为每经选清人注疏一种,另附录四种。
1962年初,中华书局编辑部形成了“《清人经解辑要》整理出版计划(草案)”,并印发征询有关方面的意见(62编字第299号):
为了满足研究工作者的需要,我局拟对清人经解的主要著作进行整理,现附上计划和书目一份,希就以下几点,提示意见:
(1)这一套书只包括清代汉学家著作,宋学家解经著作拟另行整理。这种做法是否合适?您认为书目有哪些需要增删的?
(2)各书采用什么版本作底本合适?校勘工作作到什么程度?
(3)请推荐各书的您认为最合适的整理者。
您还有什么其他意见,也请一并见示。您的意见盼于三月底以前掷下。不胜感荷。
此致
敬礼!
中华书局编辑部1962年2月22日
所附“《清人经解辑要》整理出版计划(草案)”除第五条为选目外,前四条如下:
一、经书是我国的重要古籍。清代汉学家解经,成就超越前世。但清人解经著作的刊本现在大多不易购得,为便利研究工作者参考起见,兹将清人解经的主要成果,编为《清人经解辑要》,整理出版。
二、这里所谓经书是广义的,除“十三经”以外,还包括《大戴礼记》、《逸周书》、《国语》和《说文解字》。
三、整理工作的体例将另行拟定。
四、这一套书以丛书形式出版,但暂不列丛书名称。
中华书局编辑部于3月15日收到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汇总寄回的书面意见,依次为屈守元、魏炯若、雷履平、张白珩、刘念和、徐仁甫、汤炳正、刘君惠八人,均为各自亲笔,写于3月9日。其中屈守元、汤炳正二位先生所提意见最为周密。
屈守元先生提了六条意见:
一、既名《清人经解辑要》,即非“十三经新疏”之类,因而用不着对每一部经书平均照顾,选入一些第二流(如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等)、第三流(如朱彬《礼记训纂》等)著作。
二、清人经解的权威著作如《经义述闻》、《广雅疏证》决不能遗漏。
三、易类只印惠、焦之书已足。书类孙疏不如王鸣盛、江声二家,王氏《参证》更无可取。《逸周书》有朱可以去陈。诗类陈、马、胡三家同印甚好,王氏《集疏》反不如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精当通用。《礼记》清人所作不能超过孔疏,可以不用朱书勉强备数。春秋类可以增加苏舆《春秋繁露义证》。《说文段注》应附冯桂芬《考正》。
四、皮锡瑞《孝经郑注疏》误为《孝经郑疏补》。
五、是否可以先印正续两《经解》(用缩印的办法,如印《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那样),全部供应,也可择最要者单行。然后组织力量编选《清经解三编》(用影印的办法,择原刻本或精刻、精校本缩印,开本大小与两《经解》一致)。若能如是,对学术界的贡献,比这个辑印的计划大得多。
六、如果这一套书要整理的话,请特别注意断句的工作。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左传旧注疏证》句读错误的地方太多。
汤炳正先生提了三条意见[5]:
1,在体例方面,如果依照旧例,小学附入经学,则《说文》、《尔雅》之外,应当增加《广雅疏证》、《方言笺疏》等书,同意刘念和的意见。如果将来还要整理出版清儒有关小学的著述,则这一套书内可以不收《说文》。至于《尔雅》为解经之作,当作别论。
2,选目方面,今古文家兼顾,比较精当。王先谦在《尚书》方面无成就,《尚书孔传参证》是否可以换为王鸣盛的《尚书后案》为恰当。
3,如果将《说文》收入本编,则在段氏《说文解字注》之后,是否可以援《大戴礼》之例,把钮树玉的《说文段注订》、徐承庆的《说文段注匡谬》附在后面。
另外几位先生的意见中,魏炯若推荐罗孔昭,徐仁甫说罗孔昭可以整理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或《大戴礼记补注》、《大戴礼记解诂》;雷履平建议扩大范围,将《经籍篹诂》、《经义述闻》也收进去,并建议编《皇清经解》正续编的索引;张白珩建议加上徐乾学《读礼通考》;刘念和说既已选《说文》,《方言疏证》、《方言笺疏》和《广雅疏证》也应收入;徐仁甫建议不选焦循《易通释》,增收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王念孙《广雅疏证》、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刘君惠认为名物考订也是读经的重要手段,如程瑶田《通艺录》一类的书,可以选入一两部。
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杨向奎先生也对选目提出了增删意见,并做了如下说明:
陈逢衡《逸周书补注》作得不好,没有什么用处。关于《逸周书》还是孙诒让的《周书斠补》(有家刻本)好。刘师培的《周书补正》等也有可采。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改字太多,殊嫌武断。此书可重作。
朱彬《礼记训纂》简陋,没有什么用处。《大学》、《中庸》两篇沿元人陋习缺而不注。《礼记》还是郑玄注、孔颖达疏好,后人都赶不上它。卫湜《礼记集说》、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也有用处。清末以来有些人想刻十三经新疏,《礼记》最无办法。为了成龙配套,便看上了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和朱彬的这部书。孙希旦是宋学,朱彬就更走运些。如果为了成龙配套,目前只可印此书(此后也不会有人作《礼记》新疏,低手作不了,高手不肯作。《礼记》内容太乱,事实上也没法作),否则便不当印(此书流通尚多,有家刻本,清末以来石印本,四部备要本等,好买),不如印卫湜《礼记集说》、杭世骏《续礼记集说》还有些用处(各家佚说多赖此以存)。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偶有比孔广森详细的地方,从大体看印不印没有多大关系。建议印几种难觅的《夏小正》,如宋书升《夏小正释义》(叶景葵有抄本现在上海图书馆)、雷学淇《夏小正经传考》、《夏小正本义》(有家刻本)等。
秦蕙田《五礼通考》清代有些作官的人对此书评价极高,几乎皆备此书,因为礼是国之大事,读此可以为当时政治服务。今日看来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考三代的礼有专门的书很多,秦汉以下的礼皆是沿袭虚文,又不必讲。建议印王绍兰的《礼堂集义》(原稿在上海文管会或图书馆,有自序见《许郑学庐存稿》),这是一部大书,汇集几百家之说,对研究三礼会有一些用处。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此书无用。建议印王树柟的《左传疏》,闻原稿在北京图书馆。
钟文烝《谷梁补注》此书不好亦无用。建议印柯劭忞《谷梁传注》(有北京大学排印本)。
除对上列诸书的意见外,杨先生也建议增补王念孙《广雅疏证》并附校补札记等。
对照《十三经新疏》和《清人经解辑要》两份目录,主要的差异之处有两项:一是后者取广义的经书概念,除“十三经”以外,包括了《大戴礼记》、《逸周书》、《国语》和《说文解字》;二是各经没有严格限定入选著作的种数。也因此学者们所提意见,范围更加扩大。在这份计划草案发出之前,负责哲学组工作的傅彬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将自己的想法向金灿然作了书面汇报:
灿然同志:
昨天傍晚,收到关于整理印行清人注疏本的各项文件。今天向严(健羽)同志问清经过情况后,又重新看了一遍。认为计划定得太大,还是照您指出的第一点“就顾的方案,吸收童、章的意见”,另拟方案好。这套书的名称,也待研究,最好还是用上“十三经”字样,与“二十四史”、“四书五经”等名称相对。内容仍以原“十三经”为限,《孝经》仍然保留(让大家见识见识《孝经》也好,我没有读过《孝经》,也从没有翻过《孝经》,到前年拿来翻了一下,才知道是怎么样的书)。《尔雅》是字书,与他书比,思想性较少,但既然原来列入了,还是让它保留。每经以一种为原则,必要时可另加一种,如《孝经》、《尔雅》就不必加了。总数限定在二十种以下,每种书重复不超过一种。硬性规定,比较好办。照现在的拟目发出去,让这么多人提意见,将会搞得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旷日持久,反而妨碍工作。今天先向您提出这个原则,如认为可以考虑,再来定名称、拟目,定做法,然后去请教别人。如果确定这样做,就由我来负责,一个星期之内向童、章等商量,提出初稿。匆匆不尽,余容以后详陈。此致
敬礼
傅彬然2,16下午
此函中两次提到的“童、章”,是当时哲学组老编辑童第德、章锡琛先生。在原信末行有傅彬然亲笔:“原信字迹写得太草率了,怕看不清,烦季康同志重写。”另有纸条补充说明如下:
刚才写奉一信,再补充几句,关于印行清人经解,我现在的想法,和过去有所不同。原因一则从传统“十三经”这一名称着眼;二则新增加《国语》、《逸周书》等,道理并不顶充分,前二者是史书,后者(引者案:指《说文解字》)是字书。再致
灿然同志
傅彬然二、一五下午五时半
傅彬然的意见当时应该是没有被接受,所以才有前面已经述及的印发计划草案征求各方意见的事。
《清人经解辑要》的计划在陆续收到各方面意见之后,还在不断商讨之中。在我们从网络购回的档案中,有傅彬然《重印十三经的一些想法》两纸(另有他手抄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清十三经目录”一纸),其上另有给金灿然的纸条:“关于重印‘十三经’的一些想法,请灿然同志核定。傅彬然4/10。”金灿然批示:“第一件事同意,请即办。第二件事待第一件有眉目后再办[6]。金5/10。”[7]
傅彬然《重印十三经的一些想法》共四条:
一、选清人注“十三经”一套,名《清人十三经注疏》,选目拟以尹炎武写缘起的为主,请童第德、顾颉刚、陈乃乾等同志一商。所以不称“清经解”,因为这名称看起来范围太广。《皇清经解》、《续经解》不附原经全文,将来可考虑选印。——清经解可印者似不能限每经一种,这一套出版以后,仍然可以续出单种。
二、杨、张拟目第二辑中各书,不必一定称“经解”;关于解经部分,多收入“经解”;其中多数可作读书笔记出,陈乃乾同志有此计划。
三、《清人十三经注疏》的印行方法:选择善本,断句印行(经文依黄侃短句)。开本大小、装订,仿“二十四史”。这套书的目的,供新专家阅读,能全用新式标点重排更好。
四、“十三经”白文,作工具书用,照黄侃校本印行,与此配合,另编索引。
原件附抄了尹炎武执笔的《汇刻十三经义疏总目录及缘起》5页,末署“民国廿二年十月丹徒尹炎武石公记于旧京后泥窪之繙经室”。汇刻“十三经义疏”由陶湘创意,杨钟羲、张尔田、傅增湘、陈垣、董康、孟森、丁福保、闵尔昌、高步瀛、胡蕴玉、吴承仕、邵瑞彭、余嘉锡等二十余人参与商定,《缘起》云“日夕商榷,书问十返,各屏异执,成兹总目”,共五百卷(附录在内)。但“雕造须时,糜金十万(全书都一千二百数十万字,需款十万以上),一人一地,必难独任”,最终未能印成,仅有朱印样本一册留世。
从傅彬然所提四条,可知当时有分辑出版,并另印“十三经”白文的计划(杨、张拟目未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傅彬然在此第一次采用了“清人十三经注疏”的丛书名,后来一直沿用的整理和出版形式也已基本确定,并且得到了金灿然的同意。
事情要再往前回溯一下,中华书局编辑部1962年2月22日具文发出征求意见的《清人经解辑要》计划草案,同时也呈报文化部党组书记、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征求他的意见。齐燕铭于同年10月1日作了如下批示:
灿然同志:我认为这步工作暂时可以不作。因为:这些书大多数为近刻,易得。经学还没提到研究日程,如何研究也还值得考虑。其次,如此计划所列的书,体例不一;如一般涉猎,并不便于初学;如为专门研究,又感不足。如何办,可以迟一些时候看看学者需要再来考虑。齐燕铭
齐燕铭是章门弟子吴承仕的学生,于经学当是内行,所以才有这一番关于“初学”与“专门研究”的评估。其实,更要紧的可能还是“经学还没提到研究日程,如何研究也还值得考虑”这句话。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都占据统治的地位,但与当下“古为今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宗旨,却不甚相符,时机尚不成熟,这也许才是“这步工作暂时可以不作”的真正原因。金灿然看到这个批示,应该不无意外,因为他刚刚在傅彬然《重印十三经的一些想法》上写了“请即办”的批示,现在又在齐燕铭的批示后面写下:“照齐批办。”这一天是1962年10月5日,“清人十三经注疏”的计划被叫停。
十年之后,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重新启动,由顾颉刚总其成。周总理派吴庆彤同志到他家看望,并转达总理对“二十四史”标点工作的重要指示。在另一次会议上,总理提出:“不但二十四史要标点,十三经也要标点。”[8] 又过了十年,1982年,中华书局重新启动“十三经清人注疏”丛书,在这年5月起草的《十三经清人注疏出版说明》后,附录了列入丛书的24种书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选目综合了《四部备要》本清人十三经书目和尹炎武等“十三经义疏”、顾颉刚“十三经新疏”的拟目,尤其是承续了在“清经解辑要”拟目及各方意见基础上傅彬然提出的“清人十三经注疏”方案,可以说“十三经清人注疏”丛书计划,是中华书局编辑部和过去几代学人编纂设想的汇结。
2012年4月4日,清明
2012年4月17日晚改
附录:十三经清人注疏选目对照表(略)
[1] 顾颉刚《拟印行〈十三经新疏〉缘起》,抄本。
[2] 《谈印书》,《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5日。
[3] 陈金生《二十八年为书忙——述哲学编辑室的工作历程》,《回忆中华书局》下册,85页。中华书局,1987年。
[4] 此信《顾颉刚书信集》失收,所据为网络图片。
[5] 《汤炳正书信集》收录,8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
[6] 傅彬然所说第二件事为:“又,拟印《二十二子》。一天,与顾颉刚同志闲谈,他提出影印浙江书局版《二十二子》,我以为颇可考虑,主要作工具书用。《诸子集成》式的将来还是要作。”
[7] 原件没有明确的纪年,根据内容推测,应是1962年10月5日。
[8] 《光明日报》1979年3月6日。
(刊于《书品》2012年第三辑。发表时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