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业界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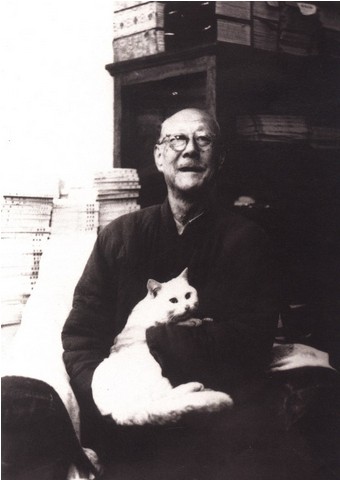
他出身于显赫的官宦世家,他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清室贵胄溥侗、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大公子”;他热衷于书画鉴藏、诗词、戏曲;他淡泊名利,终身追求传统文人的最高境界;他爱国至诚,为国家捐献了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国宝级文物。一个世纪以来,他成为广受知识界、文化界敬仰的“中国文人”。他便是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的民国奇人—张伯驹。
近年来,记述、描写张伯驹的图书目不暇接。然而,大多停留于张伯驹的生活经历,诸如生活离奇、收藏书画出手大方,甚至不惜发挥想象,描写其出入青楼歌馆,借以媚俗。能够深刻揭示张伯驹内心世界、人生境界、精神品格的,不是很多。有之,则要数近期三晋出版社出版的寓真先生所著之《张伯驹身世钩沉》。
寓真先生此著,延续其《聂绀弩刑事档案》的撰写路径,以披露独家史料见长,而侧重于“钩沉”。
所谓“钩沉”,即稽考史料,探索道理。寓真先生善于此法。其《张伯驹身世钩沉》之钩沉,特点有三:
“钩沉”之一,搜集独家史料,加以稽考,揭示其身世之谜。
本书的前言,寓真先生开门见山地说:“对于张伯驹的事迹,广大读者并不陌生。但许多人也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张伯驹的事迹,读者津津乐道的,是其民国年间优雅的生活,民国以后坎坷的经历,以及酷爱收藏,并捐献一生所藏,等等。本书所“钩沉”的,重在张伯驹的“身世”。其一,以大量笔墨揭示张伯驹之父张镇芳的生平,揭示出张镇芳忠于亡清、干练明达的个性,同时,为揭示张伯驹的身世作了导引。
关于张伯驹的身世,寓真先生将读者熟悉的部分几乎全数隐去,重点钩沉其“情曲微露”的内容。最为豪爽的,当数张伯驹在上海“青楼夺姝”,将潘素取归己有;最曲折离奇的,当数张伯驹在沪上被黑社会绑票;最令人痛心的,要数张伯驹家事纠缠不清,屡屡对簿公堂;最感动并感叹的,要数张伯驹将所藏文物几乎悉数捐献,“最终成为无产者”;最使人伤心落泪的,是张伯驹等人,雅集承泽园。其中种种委曲,多半取自第一手史料,令读者目不暇接。比如张伯驹与其前妻王韵缃、妹妹张家芬的纠纷,大部分史料取自公堂对簿中的记录,是不易得之的。
“钩沉”之二,揭示张伯驹作为文人的特别禀赋、精神、气质。
本书的“文外前言”说到:“如果我们只是复述张伯驹先生那些利国的好事,似乎并无必要;然而,当我们透过行为现象,观照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却会是别有意趣的。”这是作者写作动机的告白。事实上,有关张伯驹的文物收藏及捐赠国家,及其一身的许多显要经历,都在作者的笔下省略了。他只是截取了张伯驹身世的背景、张伯驹的家事纠纷、张伯驹接受改造的某些片段,作深度的钩沉。当我们看到张伯驹一家复杂的关系、妻妾近似腐朽的生活时,即可以进入他的精神世界,理解他决绝的几乎要逃离这个家庭的生活态度,而家事的纠纷确实给他增添了许多烦恼,最终是“纠纷解决,却恨腰缠输尽”。不久,在他捐出八件珍贵文物后的翌年,却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时,张伯驹已经卖掉承泽园的房产,住进后海南沿26号。他被挤到尽东头的一二间屋里,原有的好一些家具,也一无所有了。尽管如此,张伯驹对文物收藏的痴迷、对捐献祖国文物的行动并无悔意。他是真正爱着祖国、爱着祖国的文物。所以,作者说:“也许,只有真正的文化人,不会为金钱所迷惑。他们甘于淡泊,甘于清贫,苦苦地守卫着列祖列宗们遗留下的文化。文化不能当鲍鱼吃,不能当洋酒喝,不能当别墅住,不能当高级轿车坐,文化人不得不守护着,是因为那里有我们民族的灵魂,而这民族的灵魂,是也已经浸润到文化人的灵魂了的。”这正是张伯驹作为文化人的精神品格,是我们当代人应该予以坚守的。
“钩沉”之三,以“多余的跋语”交代写作意图,在其第一段:“笔者以为,我们来认识张伯驹的思想品性是怎样形成的,这是基础;后来的事情便如同顺流而下。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身世基础,单言后期之事,单看他后期写的那些交代材料,甚至会发生某些误解。张伯驹既要应对政治的压力,迎合时代的要求,又绝不会失去一个文化人的传统信念和人格自尊。”之后,“词魔情痴,演成昆曲传奇”,“世态暖寒,感叹曲终人渺”,写他与诗人胡苹秋的传奇交往,以及师从余叔岩学戏的经历,继续“钩沉”了张伯驹作为“旧式”文人的生活历程和情趣,是必要的补充。末尾以“人性文化,精髓薪尽火传”,直接进入议论,解读作者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人的理解。对于了解本书的意图及价值,是一把锁钥。
寓真先生此书,是下了一番“钩沉”的辛苦的。所谓钩沉,必然有史家的慧眼,文学家的表现手段。这些,作者在写作《聂绀弩刑事档案》时,已经显露,在《张伯驹身世钩沉》里,得到进一步证明。所以,此书具备三个特点,可以将书尾的简洁的宣传语总结:
沧桑国史,纷纭家事,张伯驹鲜为人知的身世资料;
解读人物,阐扬文化,《聂绀弩刑事档案》之姊妹篇;
高节深人,醇儒真知,不只涉及文物书画和诗词戏曲。
(《张伯驹身世钩沉》,三晋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定价:38.00元)




















